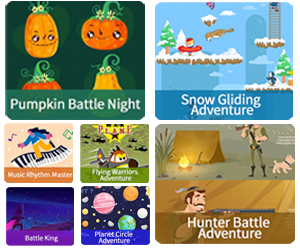元朝政权的特殊性质使得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,都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。这些译职人员的来源、选拔方式以及他们的素质,都是研究元朝翻译制度时不可忽视的问题。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制度的运作效率,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译职人员的社会地位,因此值得深入探讨。

通事与译史在元朝的官制体系中,均属于胥吏的范畴。要研究译职人员的选任及其地位,我们首先需要对胥吏的地位和任用方法有一定的了解。
元代的胥吏地位与汉族王朝时期大有不同。在中国历史上,官与吏的身份通常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,官员多出自中上层家庭,而吏则主要来源于市井小民。在法制上,吏通常被视为低级职务,进入吏职后很难晋升至更高的品级,士人往往视之为异途,宁愿在乡野度过一生,也不愿屈身为吏。然而,元朝的官吏制度则没有明确的阶层区分,二者之间的界限并不如以往那么鲜明,且两者之间的职位和权力常常交错重叠。

尽管胥吏本身没有固定的品级,但在元朝,只要考试合格,就可以晋升为官员,最高可升至五、六品。元代选拔人才时非常看重“根脚”,即个人的家庭背景。那些与皇室关系密切的家族,往往能垄断政府中高级职位。中下层的官僚则多来自胥吏,其中不乏有胥吏晋升为高级官员的例子。

作为胥吏的一部分,通事和译史的任用方式与其他普通胥吏类似,但由于译职工作需要掌握特殊的语言技能,因此他们的来源和选拔标准有所不同。尽管通事和译史都从事翻译工作,但二者的职能有很大区别。译史主要负责文字翻译,需要精通蒙汉两种文字(回回译史是例外),而且这项技能通常需要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。而通事则主要负责口译,工作内容与文字翻译不同,这些人可能只精通两种语言,却可能并不识字。在元朝多元化的社会中,这类口译人才的培养不一定依赖于学校教育。

因此,译史与通事的选拔标准和任用方式差异很大。译史的来源可以分为以下几类:第一类是通过学校考选,主要从蒙古和回回的学校以及翰林院的学生中选拔。元代设置了蒙古国子学、蒙古字学和回回国子学,旨在培养精通语言和翻译的专业人才。以洪金富的研究为例,设立在京城的蒙古国子学在最盛时,学生人数达到五六百人,地方上也设有蒙古字学。虽然并非所有地方都设有字学,但全国的学生总数仍然可以满足对译职人员的需求。然而,能够毕业并参加翰林院考试的人并不多。根据《元史·百官志》的记载:“上自国学,下及州县,举生员高等,从翰林考试,凡学官(即字学教授及学正)、译史取以充焉。”可以看出,译史的选任主要依靠国学及字学的教育背景。

根据现存资料,几位通过学校出身的译史值得提及,如张士杰、张震、王珪和秦起宗等。张士杰出生于汤阴,通过蒙古国子学进入官场,最终成为北庭都元帅府的译史。张震则从小学习蒙古国子学,并在年少时便进入中书省担任书诏史,后任译史。王珪和秦起宗也是通过类似途径进入政府工作,担任译史等职务。

回回字学则仅在国子学设有,而无地方字学。回回国子学的设立时间较晚,始建于1289年,主要为蒙古及回回高层子弟提供教育。直到1325年,回回国子学的规模仍然较小,只有约五十名学员,虽然如此,这里培养的翻译人才还是为官府提供了不少译史人选。

第二类来源是职官转充。这种情况在元代官制中并不少见,不仅低级官员可以升任官职,职官也可通过转任为吏,甚至转任为译职。忽必烈时期已有职官转充的制度,但通事和译史并未纳入其中。直到武宗改革吏制,通事和译史的任命才开始包括职官转充这一途径。根据改革规定,职官转任的译史必须具有蒙古或回回语言能力。现存资料中,秃满答和张士杰等人就曾通过职官转任的方式成为译史。

第三类来源是蒙古书写人员的升充。蒙古书写虽然职位较低,但也有机会通过任职满三十个月后,升为高级译史。例如,李彦敬便是通过这种方式,从蒙古书写转任为殿中司的译史。类似的情况还包括程遇和李师尹等人。

与译史的选任相比,通事的任用方式更为灵活。通事的任命不要求正式的学校教育,也不需要经过翰林院的考试,而是由各地官府根据需求选拔。元代初期,中书省便规定通事应具备深厚的语言能力和良好的品行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通事的选拔标准逐渐规范化,并与其他官职的选拔方法相似。

现存史料显示,许多通事不仅精通多种语言,还具备汉学造诣。例如,蒙古通事秃忽赤不仅精通蒙古语,还能熟练掌握儒家经典,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。此外,许多汉族通事也精通蒙古语言,能够担任翻译工作。

总的来说,元代的通事和译史虽然大多来自胥吏体系,但由于其特殊的语言技能和文化背景,他们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较高,且有不少人通过译职晋升为更高级的官员。虽然并非所有译职人员都能胜任工作,但许多人凭借精通多种语言,尤其是汉学和蒙学,成为了元代政府中的重要成员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